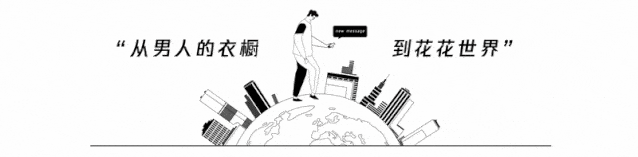
在12月25日的《脱口秀反跨年表演》中,杨笠的段子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刷屏般的反响。次日脱口秀演员池子的微博“脱口秀肯定不是杨笠那样”将这个话题推上了热搜,一封举报信的截图也让大家对这件事的讨论达到了峰值。
和今年才刚开始在脱口秀领域冒头的杨笠、李雪琴等女性脱口秀演员相比,美国的女性单口喜剧已经发展了很多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尺度大闻名的亚裔女脱口秀演员黄阿丽(Ali Wong)。尽管身处不同的舆论环境之中,杨笠和黄阿丽们的经历,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在杨笠因为脱口秀中的段子引起争议后,很多网友都提到,和满口都是荤段子的黄阿丽相比,杨笠的冒犯真的不算什么。近几年,亚裔脱口秀演员黄阿丽因在网飞播出的单口喜剧特辑《眼镜蛇宝宝》与《铁娘子》一炮走红。在她的身上,有诸多的标签,越南-中国混血的亚裔女性美国人、职场妈妈等。在这些标签之下,她在脱口秀中所展现出的辛辣与幽默则让人更加印象深刻。
黄阿丽总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一个个头不高,戴着眼镜,穿着豹纹的孕妇。因此,亲子话题自然也成为她表演内容的重头戏。在这个话题上,黄阿丽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脱下“母亲”这一角色的神圣外衣。她毫不顾忌地调侃着,如果飞机失事,她一定要先给自己戴上氧气罩,然后再给女儿戴上。在表演中,黄阿丽总是直接地打破想象中的“温馨”,比如她曾经事无巨细地描述着给女儿换尿布的种种“折磨”:女性需要24小时保持嗅觉的灵敏以便在女儿拉屎时做出第一反应;她将“母乳喂养”形容为一种磨难,她用《荒野猎人》中被野兽摧残的小李子来形容被婴儿“蹂躏”的乳房。

除此之外,黄阿丽更以一种戏谑的方式直接指出生育这一过程对女性身体带来的直接影响。她以hip pop的方式描述生产过程中,婴儿循环往复的“进进出出”;她在生产前被所有的女性朋友提醒,要在医院多“偷”一点特大号医用成人尿布,因为这种尿布只有医院才有。黄阿丽并没有止步于在脱口秀表演中吐槽生育话题,而是将其进一步上升为一种社会表达:对“产假”的呼吁,“产假是用来给新妈妈们遮掩与恢复她们被损害的身体。”

在两性关系上,黄阿丽同样火力全开。她以泼辣和胆大的作风解构了两性关系中的“性”与“婚姻”。比如“第一次约会是否要发生性关系”这一主题,她就作出了形象的对比,如果女性很快与一个男性上床,那意味着她们已经将这个男性排除在结婚的可能之外;而如果一个男性不急着与女性上床,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缺陷。在黄阿丽的表演中,类似的桥段数不胜数,但在这些看似“大尺度”的噱头之下,实则表达的是女性要在“性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的一种态度。
被黄阿丽在表演中吐槽得最狠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她的老公。她老公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结婚前,老公的父母让黄阿丽签下“婚前协议”;结婚后,黄阿丽一炮走红,成为赚钱更多的那一个,而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份“婚前协议”,老公如果与她离婚,将会净身出户。因为在经济上胜过老公一头,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母亲的质疑,她的回应则是自己帮老公承担了“养家的压力”,而老公也对此甘之如饴。与此同时,黄阿丽“保证”自己不会像那些“成功的男性喜剧人”一样,人到中年再娶年轻娇妻,她希望能长久维持自己的婚姻,因为没有人比她老公更熟悉自己那方面的爱好。
黄阿丽的脱口秀虽然充满了大胆露骨的荤段子,也常常辛辣直接地抨击两性间的不平等现象,但她的炮火通常只对准某个具体的个人,这也大大减少了对男性观众的冒犯。
她通过极其私人化的口吻来讲述具有争议的普遍性话题,又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揭开了曾经很隐秘甚至“羞耻”的关于女性的多重面纱。比起冒犯,黄阿丽更多是在“祛魅”,她祛除了父权社会赋予“母亲”与“妻子”的“神圣职责”,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酷炫的,有意思的女性形象。有意思的是,尽管黄阿丽在脱口秀中极尽嘲讽与吐槽,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又完美地契合了当代人对于“完美女性”的想象——既拥有成功的事业,又保有幸福的家庭。

但另一方面,黄阿丽的成功同样面临着诸多质疑。她首先要克服的是“女人不够搞笑”的偏见,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女性喜剧人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女性喜剧演员Aditi Mittal便曾被告知,不要将自己塑造得太过“女性化”,要尽量去性别化。在中文中,“女丑”则被用来形容女性喜剧演员,《康熙来了》便曾以“女丑”为主题制作特辑,在这一集中,几位女性喜剧人为了达到“搞笑”的目的各出奇招,颠覆形象与“扮丑”则成为前提。即便是小S,也曾多次在节目中自比为“小丑”。

表演中的Aditi Mittal
由此也可看出,“漂亮女人不好笑”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喜剧演员Christopher Hitchens便曾不加掩饰地表露过“女性不搞笑”的观点。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女性想要成为喜剧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似乎便是与“美丽”划清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搞笑的女性仿佛应当学会“取笑”自己的外形,英国女性喜剧演员Miranda便因高大的外形而自比为“金刚”,这似乎成为了一种策略。
除了之外,对于女性权益的关注也让这些女性喜剧人们屡屡受到来自男性的批评,黄阿丽便曾因为屡屡谈及生育与母乳喂养等问题受到指责。而她显然不赞同这种仅仅依据性别去定义一个人的行为,在接受Elle的采访时,她抱怨自己总被问到“作为一个女性喜剧人是怎样的感受”,“白人男性从来不会被问到,作为一个电影中的白人男性是什么感觉?”她认为,脱口秀中可以讨论的话题是没有界限的,是否被讨论只取决于自己是否有能力使这个话题变得有趣,“我很愿意去谈论政治,但是我还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搞笑的段子。”
加拿大喜剧人Daniel-Ryan Spaulding便就这些针对女性喜剧人的偏见戏仿式地制作了一个视频——《男人搞笑吗?》。在这个视频中,一位男性观众对一位男性喜剧人表达了喜爱,因为他并不像其他的男性喜剧演员一样,不停地提及“男性权益”,他被称赞为,“更像一个女性”。而在现实生活中,情况显然是截然相反的。黄阿丽的出现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整个行业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喜剧演员的数量是相当少的,根据feminism in india的报道,在纽约著名喜剧俱乐部Carolines中,女性表演者仅占20%。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女性喜剧人在这一行业中遭受了性骚扰。根据英国媒体The Guardian的报道,英国喜剧行业存在着系统性的性别歧视,这一行业仍然由男性主导,性别歧视的言论被认为是“段子”。一些女性喜剧人甚至遭受了性侵,Nina Gilligan便讲述了自己在工作中所受到的性侵。基于这种状况,一些喜剧俱乐部开始制定一些新的反骚扰政策,但效果如何,仍然未知。
知名的美国男性喜剧演员路易·CK(Louis C.K.)也曾受到类似的指责,2017年,五位女性喜剧演员通过《纽约时报》指控路易·CK在她们面前手淫,随后他承认了这一行为,他在好莱坞的事业就此停滞。但今年4月,他带着自己全新的脱口秀节目Sincerely louis C.K.回归,在节目的最后,他更是坦承“我爱打飞机”。路易·CK一如既往地具有冒犯性,但这一次他的冒犯收获的不再是笑声。
很显然,女性喜剧人们正在努力推倒人们心中的墙,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们所要突破与克服的还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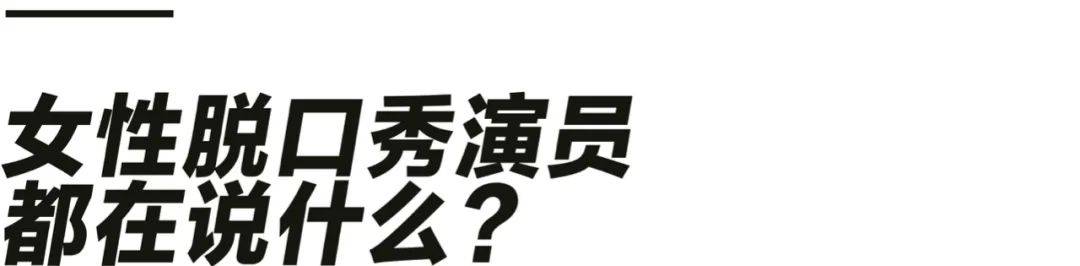
脱口秀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冒犯”的艺术,资深脱口秀表演专家格雷格·迪安在《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一书中提到:“幽默感是一种应对痛苦的方法,喜剧潜藏于痛苦的事情里,而这些领域是不讨人喜欢的。”对于女性脱口秀演员来说,冒犯男性的同时,大量有关女性身份的自我嘲讽同样是她们创作的素材,脱口秀里大量辛辣露骨的段子也让很多女性敢于在公开场合谈论“性”。
随着美国反性骚扰运动的不断发展,脱口秀也为很多深受其害的女性提供了一个表达与宣泄的出口,越来越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开始尝试在自己的表演中加入性侵、性骚扰相关的内容。这种尝试在开始的时候的确常常引起了一部分男性的不满与抵制,韩裔女性单口喜剧演员赵牡丹(Margaret Cho)曾在2015年把自己幼年时受到性侵的经历写成歌曲《我想杀了我的强奸犯》。在Stress Factory的一次表演中,她由于多次讲述自己被性侵的故事而激怒了很多现场的观众,尤其是白人男性观众。

赵牡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众在采访中提到:“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笑料(punchline),只是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故事,并且在现场高呼‘杀死强奸犯’。”在一个视频中,赵牡丹对着台下纷纷离场的混乱人群高呼:“我是不会退票的,你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当然,后来Stress Factory的员工表示,他们确实因此给不少观众办理了退票。
2017年,美国的反性骚扰运动迎来了一个高潮,而在那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站出来讲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卡梅伦·埃斯波西托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拍成一部名为《强奸笑话(Rape Jokes)》的短片,在接受采访时她也提到,自己曾经不想把这段经历公之于众,但是在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性侵事件被披露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有义务站出来。
“这让大家不再因为说出性侵经历而感到羞耻,也教会我们如何和大家谈论性。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教育、对话。”
脱口秀为深受性骚扰困扰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反抗的平台,但这种以引人发笑为目标的喜剧形式,常常变成一次对演员的二次伤害。
澳大利亚脱口秀演员汉纳·盖茨比(Hannah Gadsby)在2018年的告别秀《娜娜》曾经为观众解构了单口喜剧的本质。
在演出中,汉纳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女同志身份的笑话。十年前,酒吧打烊后的半夜时分,她在车站等待回家的末班公交。等待过程中,她和身边一位女生聊天。突然间女生的男朋友冲过来推她并辱骂她:“滚远点,你这该死的基佬(faggot)。离我的女朋友远点,你这个怪胎。”而在发现汉纳是一个女生以后,男生连连道歉:“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以为你是个想泡我女朋友的该死的基佬。”
这个笑话引起了全场哄笑,但这并非是故事的结尾。在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汉纳告诉大家,当男生发现她是一个女同志后告诉她:“我懂了,你是个女同志。我有权利狠狠地揍你。”事实上,他也确实狠狠揍了汉纳一顿,而当时的汉纳也没有勇气报警。
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具伤害性、也最需要被讲出的部分,但为了保证好的喜剧效果,汉纳在讲述的时候总是会删掉结尾的部分。她借此也和大家剖析了单口喜剧的结构,一个完整的故事分为开头、中间和结尾三部分,但能制造喜剧效果的往往只有前两部分。作为脱口秀演员,为了让台下的观众发笑,她会删掉最有升华效果、也最能引起反思的结尾部分。

“后见之明(hindsight)也在结尾部分,可笑话的运作机制恰恰相反,笑话意味着剔除和删减,在复杂程度、背景和道德标准方面的删减。”而在她看来,仅仅为了博人一笑而删掉故事中更具有复杂性的部分是一种毫无必要的牺牲。
在演出中,汉纳也提到,这些讲给观众听的笑话早已删掉了故事中真正残忍的部分。但对于曾经的受害者来说,这种经过大量删减的效果并不能带来任何治愈的效果,甚至不能缓解她生活中的痛苦情绪。
对于很多像汉纳一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脱口秀演员来说,观众的笑声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悲伤和痛苦:“笑声不是良药,它只是给苦口之药调味的蜂蜜。”
参考资料:
The New Yorker: The Comedian Forcing Standup to Confront the #MeToo Era
Page Six: Margaret Cho loses it on stage
Vulture: Cameron Esposito Is Taking Rape Jokes Back for Survivors
界面文化:从麦瑟尔到黄阿丽:女性单口喜剧中的苦痛言说
撰文:伊平&Echo
编辑:Echo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被网贷“杀死”的年轻人